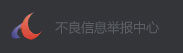-
资讯
- 时间:2021-09-26
历史上,北洋政府总理实在太多,梁士诒可能是其中不为人知的一位。除了财政与金融界的少数人知道外,他几乎已被人遗忘。但实事求是地讲,他是位很高明的金融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
中国的摩根
梁士诒(1869-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清邮传部大臣、国务大臣、铁路总局局长;曾参与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活动,民国初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素有“活财神”“二总统”之称;被当时的《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将之比作“中国的摩根”。他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集经济学家、银行家、政治家于一身。

(本文图片均为梁士诒书法作品)
在梁士诒亦官亦商的政商道路上,交通银行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驿站。1906年9月,邮传部成立,铁路均改归部辖;裁撤督办大臣,梁士诒一跃成为五路提调处提调,主持全国七分之五的铁道业务,无疑成为交通系实权人物。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他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因为,他看到借款所办各铁路,依合同规定,存放款项一向由外国银行分储,汇款亦由外国银行汇划,损失太多,因建议邮传部“设立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五百万两,招募商股六成,先由邮传部认股四成,以应开办之用,名曰交通银行,将轮、路、电、邮各局,向由洋商银行存款者,改由该行经理,就邮传部各项散款,合而统计,以握其经画之权,一切经营悉照各国商业银行办法……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是轮、路、电、邮实受交通利便之益,而交通利便,同不仅轮、路、电、邮实受其益己也”。应该说,这是创立交通银行的初衷和理想。其实,交通银行初创时,总理为李经楚,协理周克昌,梁不过是帮理。但其后因政治关系,梁于1918年6月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并手撰国民须知数千言,刊印十万册分送各地,请一致信赖与爱护中国、交通两银行,以巩固本国金融机关。特别是在北伐战争前后的南北大变局中,他灵活运筹、妥善应对,逐渐成为交行的“灵魂”人物。从这点看,他无疑是交行史上乃至中国金融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会通于意态之际
如果说,梁士诒的经济管理能力和金融理财水平得到了世人认可,如今亦为学界所关注和研究,那么作为其个人学养的书法造诣却一直被人们忽略,至今鲜有人提及。谈到民国书法,可谓“诸侯争霸、群雄四起”。在那个刚解除帝制的时期,新旧交替、西学东渐,文化与艺术得到了自由和释放。无论书法、绘画,还是诗词、文章都有了崭新的面貌。康有为、于右任、张大千、张謇、袁克文、冯超然、林长民、蔡元培、吴昌硕……他们或是掀起过历史改革巨浪的前贤,或是留洋归来拯救中华的斗士,或是善用笔墨描绘内心世界的书画大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用毛笔和书法——这一最中国、最传统的方式以墨寄心、以笔赋情,发出了时代的呐喊。诸君子之风度、气质、学识,也都蕴藏在这笔墨之中。

梁士诒在书法上的名头固然不及当时的“四大家”(谭延闿、胡汉民、吴稚晖、于右任)响亮,但若论书艺其亦不逊色,甚至比某些名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童年时代读私塾开始,他就在父亲梁知鉴和塾师的严格指导下学习书法,初学颜真卿《多宝塔》,临过颜的《争座位帖》《三谢帖》和大字《麻姑仙坛记》等,后又易宗李北海,全力临《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清华寺碑》等,一变颜鲁公之习,悟得唐人用笔之法,复上溯“二王”,间临《石门造像记》《张猛龙碑》等,将名碑法帖参互研习,书艺渐精。后梁士诒虽跻身政坛,亦无意于在翰墨上出人头地,且随着官位的不断提升,政务日趋繁忙,但其却一直都未停止过对书法的偏好与学习。好在传统意义上的书法作品,其创作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以实用为主,而不是以纯粹的艺术审美为旨归。其时,公文处理均用毛笔,正好使他习字与公务两不误。正是在这种日常性书写中,他将历代碑帖中有益的精华化为自己的笔墨语言,“会通于意态之际”(明·项穆),从而达到广览博收、取精用弘之效果。
无意于佳乃佳
从其存世作品来看,以信札、对联、扇面、横批等为主,且以楷书和行书这两种实用性书体见长。其书用笔方圆并施,线条舒展雅致,纤细而不羸弱,秀挺而富有弹力;笔画或仰或俯,或轻或重;结构严谨,欹侧而取姿秀美;字形大小参差,简繁穿插,从而形成了一种节奏明快、骨力洞达、肌腴筋健、刚劲蕴藉的艺术特色,呈现出浓郁的晋唐气象。
由于梁士诒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金融管理工作,所以对大局的预判和掌控能力胜于常人。而这种职业敏感和习惯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到其书写上来,即十分注意处理空间分割与整体布局。在他看来,写字并不难,难在布局:字有大小、繁简、长短。一句中有时几个字重叠相连,如一山复一山,或行行重行行,知之为知之等,如果在落笔前不先打“腹稿”,在挥毫途中再思索变化,就难以达到一气呵成之妙,即使每个字都写得很精彩,也不甚可观矣。

尤其是他的大字作品,虽然存世数量不多,如今能看到的仅有《谦受益》《燕京旧雨》《峄阳溪路第三声》等几帧,但件件均为精品,显示了其在布局方面的高超水平:结字奇拙、险中求胜,墨色丰富、浓淡相宜,疏密有致、虚实得当,故虽无纵横捭阖、剑拔弩张之势,但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志在必得、呼风唤雨之雍容气度。可以说,这种笔墨驾驭能力并不全是从历代前贤的碑帖中得来的,更多的是其跌宕的人生历练、丰富的交际交游和长期身处社会顶层的气度格局以及多重身份与学养之映射。而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境遇又是当时一般学人与艺术家所难以遭遇和企及的。所以,学习书法的难点不在于用笔、结字,最难把握和模仿的则是格局与格调,其与书家的学养、阅历与胸襟息息相关。当代人中学赵孟頫、“二王”者不在少数,加之印刷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名家碑帖不仅唾手可得,且质量上乘、纤毫毕露,但真正能写出原味写出格调者寥寥无几,远不像梁所处时代那样高手云集、名家辈出。其一,是主观原因。当代人由于对传统的领悟不够,当下书坛的一些所谓的“大家”,却没有“童子功”,没有坚实的根基和底蕴,导致其对传统经典的领悟不足。其二,是客观原因。今人生活安逸,经历简单,缺乏生活磨砺,又面临各种诱惑,习书之目的不纯。反观,梁士诒这一代人写字多是实用之需,并不当作是有意识的艺术创作,其本人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或以艺术家自居,更无利益之驱使。如同当代碑派大家、书法教育家陆维钊先生在最负盛名时却一再惋惜地自评:“想不到最后竟落得个书画家的下场。”这充分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整体的价值观:年轻的时候要多做学问,写字应该是业余的,但写好字这是最基本的,并无可自负或炫耀之处。而当今一些书法家却为写字而写字,为创作而创作,一些高校也为专业而专业,为学科而学科,反而使书法失去了“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本真,始终无法达到“偶然欲书”“随意落笔”却“无意于佳乃佳”之境界。
因此,梁士诒那代人的墨迹,不能用今天“展厅时代”的书法评价标准去欣赏和衡量其高下优劣,即使书者书写水平一般,亦可通过这些镌刻了独属于他们的时代记忆和痕迹之手迹,让后人一窥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市公安局备案编号:1101081994 版权所有:北京一源一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安局备案编号:1101081994 版权所有:北京一源一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